在里斯本青旅,與阿爾及利亞女人的上下舖戰爭
- Miao-Chun Lin
- Mar 23
- 5 min read

在里斯本老城區的巷弄間,青年旅舍藏在不起眼的建築裡。木門斑駁,樓梯陡峭,電燈昏黃,走進去後,混雜著異國調料味、廉價香水、洗髮精泡沫殘留的氣息,這是一個沒有歸屬感的地方,卻收容著一群暫時無處可歸的人。
我剛從台灣辦完簽證回來,為了省錢,住進這間青年旅舍,和幾個素昧平生的人共享一間四人房。常常經過櫃檯門口時,我都以為自己進到什麼黑幫的基地,裡面擠滿了來自各個國家的旅人,交錯著法語、西語、阿語、葡語,讓人分不清這到底是旅舍還是什麼收容所。
房間的下舖住著一個阿爾及利亞女生。她長髮凌亂,嘴裡叼著菸,視訊電話開得震天響。她用法語和家人說話,語速快得像打機關槍,而那音質之差,讓人懷疑她是不是在用收音不良的二戰軍用對講機交流。
「……然後呢?媽,聽得到嗎?喂?!」
她的聲音穿透牆壁,像要把整間旅舍震碎。我在上鋪翻了個身,試圖壓抑煩躁,但她的聲音如野狗狂吠,沒完沒了。我忍耐了一小時後終於受不了,伸手敲了一下鐵欄杆,發出清脆的「噹!」聲。
「可以不要講電話了嗎?這裡是共用房間欸。」我先用英文說。
她愣了一下,抬頭看我,然後用法語問:「你說什麼?」語氣裡滿是挑釁,像是在說:「妳是在命令我嗎?」——我到現在還是搞不懂她為什麼明明身在葡萄牙,卻每次對人開口都直接說法文,彷彿別人應該要聽懂。
她的語氣顯然沒打算停止。我深吸一口氣,改用法語回答:「我說妳的聲音太大聲了,吵到別人了。」
她瞪著我,好像我是個不可理喻的怪物,然後冷笑了一聲,開始用法文罵我沒禮貌。奇怪,看來她對於「沒禮貌」的標準與普羅大眾不同。而且如果我沒有剛好懂法文,這整段是不是就不會發生了,我也不知道。
「妳要是再吵,我就去找櫃台。」
「臭婊子。」她低聲罵道。
「臭婊子是妳。」
我們隔著鐵欄杆互罵,像兩隻關在籠子裡的野獸。她激動得拍打床鋪,嘴裡蹦出一連串阿拉伯語髒話,而我則是用法語參雜英文回敬她。這場對峙像是一場無聲的戰爭,沒有硝煙,卻足以讓旅舍的氣氛降至冰點。
我們的爭吵混雜著尖叫聲甚至驚動了隔壁房的住客,一個黑人女生敲門探頭:「妳們還好嗎?」
「關你屁事!」阿爾及利亞女生吼道,然後砰地一聲關上門。
我從來都不知道上下舖的鐵欄杆能夠形成一道結界,當下的我把那個當成我家的後花園柵欄——要是有人敢越過這個柵欄,我便可以合法地殺了她,當然,一切只是存在我腦海的想像裡。
這場戰鬥持續了將近半小時,最後我們都精疲力竭。她氣呼呼地爬回床上,而我轉過身去,戴上耳機,試圖隔絕這個讓人窒息的世界。我打開手機,卻發現自己的手正微微顫抖,憤怒與疲憊交雜,像攪拌機裡的混凝土,沉重得讓人喘不過氣。
然後,眼淚忽然掉了下來。
起初只是第一滴,接著第二滴、第三滴沿著原本的淚道順勢的滑下來。不是嚎啕大哭,而是靜靜地落淚,像夜裡滲出牆角的潮濕水痕。我的耳機裡放著音樂,周圍的一切彷彿靜止。
忽然,鐵欄杆被敲了敲。「噹!噹!」兩聲。
「喂。」她叫了我,像是國中生互傳紙條時的暗號。
我轉頭看她,眼睛紅紅的,鼻子也紅紅的。她看到後露出有點不知所措的神情。
「對不起。」她說,語氣裡沒有剛才的敵意,反而帶著一絲疲憊與愧疚。「我不該對妳大吼大叫……我不是這種人的。」
她嘆了口氣,眼神飄向天花板:「我最近在弄簽證的事,每天都焦慮得吃不下飯,只能靠咖啡和菸支撐……剛才不該發妳脾氣的,真的很抱歉。」
我低著頭,沒說話。眼淚又突然掉下來,像關不了閘的洪水。我知道自己不是因為這場爭吵才哭,而是這些日子以來的所有壓力——簽證的麻煩、旅途的不順、永遠在移動的疲憊、無處安放的情緒。這場爭執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,它剛好觸發了這場洩洪。
她見我哭了,顯得更加慌亂,愧疚地看著我:「姊妹,我對不起妳,妳不要再哭了好嗎?」她語氣急促,像是不小心弄哭同班同學的青春期國中生。
我抬起頭看她,突然覺得她沒那麼討厭了。她不是個惡意的人,只是累了、焦慮了,剛好在錯的時間、錯的地點,碰上同樣焦慮的我。
我吸了吸鼻子,低聲說:「我也很焦頭爛額,剛到葡萄牙,簽證的事…還有其他的事讓我快瘋了……對不起,我剛剛也太衝動了。」
「沒關係,姊妹,只要妳可以笑一下就好。」她說。
我的確笑了。
沉默片刻後,她忽然問:「妳餓嗎?要不要去對街吃 kebab?我請!」
我愣了一下,抹去眼淚,點點頭:「好啊。」
我們一起走出旅舍,走到對街的短短500公尺內她就抽掉了兩根菸。我看著她吞雲吐霧的模樣,心裡想著,也許她只是用這些尼古丁填補心裡的某種空缺,就像我用耳機和音樂來隔絕這個世界一樣。
吃飯時,她告訴我,她在巴黎當保母,現在想搬來葡萄牙。至於這中間的關聯性以及原因,我沒有多問。但我想起她在房間時,也一直在和小孩視訊,於是順口問:「那妳會想要小孩嗎?」
這麼私人的問題,我竟然脫口而出,連自己都嚇了一跳。平常的我不是這樣的人,萬一勾起了什麼不好的回憶怎麼辦?三秒鐘內,我的腦袋裡閃過無數種對話可能。
她愣了一下,然後露出理所當然的神情:「當然想啊,難道妳不想嗎?小孩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禮物。」
她的語氣理所當然,彷彿女人天生就該想要小孩。我嗅出宗教的氣息。
我沒有回答,只是笑了笑,低頭繼續吃飯。
我們繼續聊著一些表面的話題,彷彿三十分鐘前的爭執從來沒發生過,彷彿我們在青旅的上下舖一見如故、聊得很來似的。
畢竟大家都說,異鄉的旅行總少不了那些溫馨動人的邂逅嘛。
就當作三十分鐘前,兩個女人歇斯底里地互相咆哮、幾乎要抓著彼此的頭去撞欄杆的事,從來沒發生過吧。
就當作這是一場從頭到尾都很美好的相遇吧。
我看著她在馬路上抽菸的焦慮神情,心裡忍不住這麼想著。
回去的路上,風很大,她的帽子被吹走了。我幫她撿回來,她笑得東倒西歪,然後一把摟住我的肩,「姊妹、姊妹」地叫著,彷彿我們真的是認識多年的故人。
我們沒有交換聯絡方式,沒有說再見,甚至沒有刻意放慢腳步,好像都默契地知道,這就是一個只會發生在今晚的故事。不需要延續,也無須回頭。
旅舍門口,剛剛目睹那場怒火交鋒的黑人女生正坐在櫃檯旁,看著我們勾肩搭背走進來,臉上寫滿困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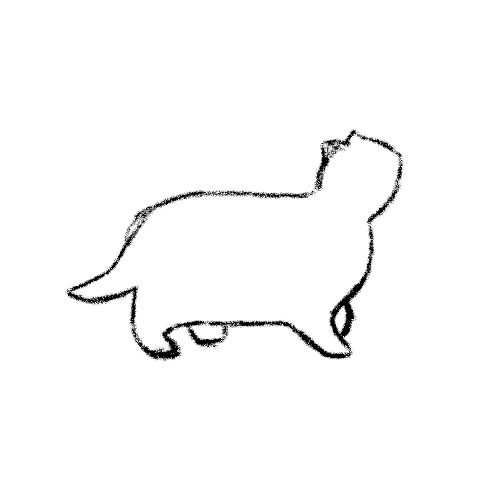



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