伯明罕、英國紳士、與世界連接的手機
- Miao-Chun Lin
- Jun 1
- 5 min read

在離開倫敦的那個灰藍清晨,我帶著疲倦與一點不確定,搭上了往伯明罕的長途巴士。車窗外的景色從密集的人群與雙層紅巴,慢慢過渡為工業氣息未散的城鎮與斷續的田野,那是一段過度也過渡的旅程,就像我此刻的狀態——既不屬於倫敦,也還沒進入伯明罕的節奏。
伯明罕的Airbnb有種「我不是壞人家,但門口真的有點可疑」的氣氛。它坐落在一條還算熱鬧的大街上,但入口卻藏在一條狹窄陰暗的小巷裡,得從餐廳的後門旁邊繞進去,再踩著一段吱吱作響的鐵梯上到二樓。樓下餐廳的員工輪番在巷口抽菸,煙霧和濃濃的炸物味混在一起,倒也不是不親切,只是其中一位員工對搭訕顯得特別執著。我那來自印度的室友也提起過他——說每次經過都會跟她講話,語氣裡有些怕,不無理由。某晚她甚至類似恐慌症發作一樣地突然把所有門鎖得死緊,說她夢到有人闖進來。之後我們進出都得彼此通風報信,產生了一種怪異又微妙的同盟感。
儘管住處稍嫌可疑,我倒是很喜歡我寬大的房間,而伯明罕本身倒也意外地宜人。市中心沿著運河展開,像是一場清晨才醒過來的夢,空氣乾淨,街道安靜,十月的陽光也還捨得露臉。我在抵達的隔天便出了門,拿著一杯 Blank Street Coffee 的熱拿鐵邊走邊晃,正準備走進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 時,一個男人叫住了我。
他說我有種「很calm的氣場」,讓他想過來稱讚我,然後就這樣,沒有其他目的地,並祝我一天愉快。英國人有時說話就像他們的早餐——簡單直接,卻不一定清楚到底飽不飽。我禮貌地回話,閒聊了幾句,原以為就此打住,他卻趁勢突然提議帶我去一間有名的電影場景咖啡館參觀,並說要請我一杯咖啡。免費的咖啡誰不愛?我當然說好。
走了幾條街,發現那其實是間裝潢浮誇的飯店一樓酒吧,如果不是當地人帶,我肯定會以為裡面只有香檳和老闆的私生子。接著他又帶我去一間高空酒吧俯瞰市區,我心想也行,反正不用喝酒,只是散步——在電梯裡遇到兩位波蘭女人,聊到我住過格但斯克,她們眼神露出那種「這個亞洲女生也太違和了吧」的驚訝。我已經習慣了。像被貼上了「為何你會出現在這裡」的標籤,久了也就學會聳肩當回應。
從高空望下去,伯明罕果然是一座有著獨特節奏的城市,然而因為我對它還沒有足夠的記憶,自然也談不上什麼顛覆印象。不知道是因為氣氛佳還是什麼原因,當那位英國男子忽然轉向我、用電影裡才會出現的英國紳士口氣問「我可以親妳嗎?」時,我幾乎沒思考便馬上回了「不可以啊。」他被我的直接給愣住,我也被他的突如其來給愣住。為了避免他誤會,我清楚表示我現在對約會沒興趣,我們可以做朋友,他說他也不缺朋友。好吧,那倒也挺坦白的。
雖然做不成「朋友」,我們還是繼續聊了些東西——他的前女友、台灣政治、中國、亞洲文化與西方社會的落差。氣氛其實很輕鬆,甚至愉快。他還陪我去亞洲超市買泡麵跟水餃,之後又一起吃了韓式石鍋拌飯,他第一次吃,覺得很神奇地美味。但我想他開始覺得我有點難搞,因為我一方面笑咪咪地聊天,一方面拒絕任何進一步的可能性。
最後他送我到車站,還幫我確認火車時間跟月台,這時距離開車還有十五分鐘。他於是問了我的手機號碼,想要保持聯絡。我說:「你不覺得一面之緣很好嗎?如果留了聯絡方式,之後只是偶爾在網路上無聊地互相點讚,那不是太無趣了?」但他沒有被說服,說在我離開伯明罕之前我還可以帶他嘗試別的亞洲料理,或者我們可以繼續再聊天散散步也無所謂。於是我靈光一閃,說:「我給你兩個選擇——一是我的手機號碼,一是在你臉頰上親一個,你要哪一個?」
他猶豫了一下,最後選擇了在臉頰上親一個。我笑了,「男人果然還是男人。」我友善地在他臉頰上啄了一下後說了再見,然後轉身小跑步往月台去趕車。
他追在後頭大喊我名字、拜託我還是給他電話號碼吧,我思忖著:哈哈,貪心的男人,最終還是什麼都想要,但已經做出的選擇就要像個男人一樣承擔。但其實不過是個手機號碼罷了。
我沒有回頭、三步併作兩步地跑下12號月台,並一腳踏上車廂。那個畫面應該很帥,可惜我坐下後一摸左後方的口袋,發現手機不在。右後方、外套口袋,都沒有——手機不見了。
我心跳加快、腦中一連串浮現他是個技術高超的扒手的可能性,又一邊狐疑地思索,覺得半天相處下來後,感覺他應該不是這種人。正當我還在驚慌失措時,火車門響起關閉提示音,我像間諜片裡女主角一樣毅然決然地衝下車,回到12號月台上,已不見他的身影,而手機也暫時沒找著。在失物中心報案過後,我一邊懷疑人生,一邊搭下一班火車回家。
回到家後我立刻用筆電開啟「Find My iPhone」定位,發現手機竟還在伯明罕市中心的火車站,沒有移動到其他地方,代表確實是我在某個時間點掉了,被人偷走的可能性變低。而我也突然覺得稍微心安,原來人性還是可以相信的。弄掉的手機位置顯示在車站裡的咖啡廳,但致電詢問卻一無所獲,我計畫明日再繼續我的尋機之旅。躺在床上的我突然沒有手機可以滑,思考著沒了手機的人類真的無法正常生活,感覺與世界隔絕,明明世界就在我眼前,我卻難以感受的到,像什麼東西斷了一樣。
隔天一早我拖著疲憊的身體返回伯明罕市中心,像福爾摩斯一樣邊拿筆電邊追蹤定位,眼看手機快沒電,心跳得比昨天還急。失物中心還是沒消息,我突然像個抓周失敗的家長一樣抓住唯一一個員工問:「那邊咖啡店找過了,都沒有,可是定位顯示就在那裡,怎麼辦?」他隨口說:「妳有看過樓下的月台嗎?」
啊對,還有月台。
我像昨日一樣匆忙跑去12號月台。正值上班時間,人來人往的,我焦急地等火車駛離、月台上像螞蟻般的人類散去後,低頭彎腰搜尋,一處一處地用我的雙眼慢慢掃描。走了幾步後,我忽然瞥見在黑暗的鐵軌上靜靜躺著一個熟悉的藍色方形物體——是我的手機。在一個紳士跳下鐵軌幫我撿起手機,再跳上月台將它交到我手上時,我差點哭出來。那是一種「與世界又重新連接上」的幸福感。被火車輾過的手機,因為安然地躺在鐵軌縫隙間,所以居然只有螢幕保護貼的角落有一點碎裂,其他部分都完好無缺,這大概是2024年九月開始的那場水逆裡,我遇到最幸運的事情了。
我為了慶祝找回手機,還回咖啡廳買了一個可頌跟一杯拿鐵,興高采烈地坐上回家的火車,準備回去補眠。結果滑開手機,只有四則訊息——三封是廣告,一則媽媽問「晚餐吃什麼呢?」原來一天沒有與世界連接,還真的沒有什麼差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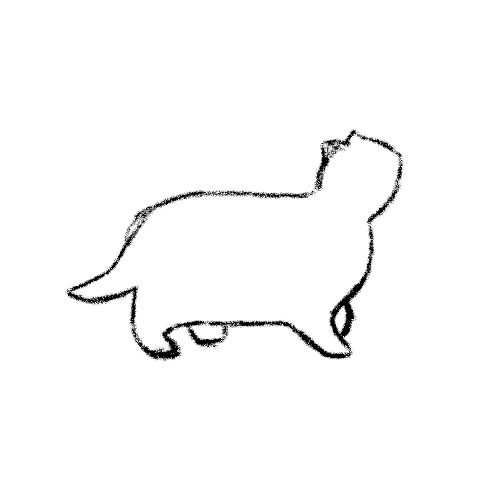



Comments